 柯平〔现代〕
柯平〔现代〕
常常 我将七月流火
视作炼钢厂沸腾的炉槽。
我写出的诗篇
多么现实。
仿佛当炉的文君
也只是隔壁个体酒店的女经理。
而霓虹灯与大厦——我的秦时明月汉时关。
我语言的蟋蟀
钻入社会主义的床下。
我在那里 在想象与愿望中
寻找我的结构 我的语调。
我称王称霸 披肩的长发上
戴着槐安国王朝贡的冠冕。
古典的春夜 我指挥意象的御林军
攻打比喻的城堡。
然而
一旦遇上边防部队的探照灯
我就溃不成军 落花流水 逃回辋川。
四点,或者是五点吧!
我在别人的鼾声中
醒着……
“多么幸福,多么甜蜜呵!
”
我祈求他的鼾声
是滚动的春雷。
而我蛰伏,
象大地深埋的一截木头
有着沉睡,有着孕育……
 洪炳文〔现代〕
洪炳文〔现代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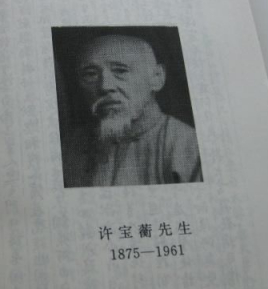 许宝蘅〔现代〕
许宝蘅〔现代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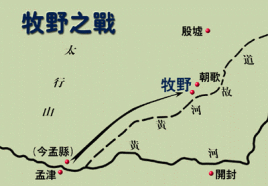 牧野〔现代〕
牧野〔现代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