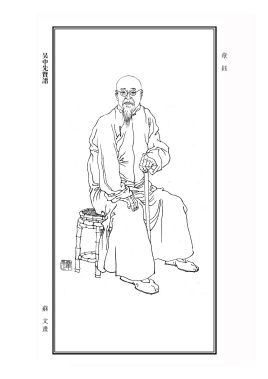 章钰〔现代〕
章钰〔现代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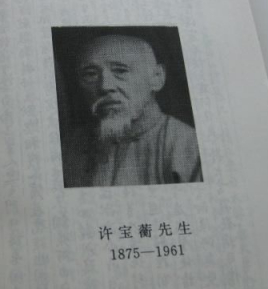 许宝蘅〔现代〕
许宝蘅〔现代〕
 胡续冬〔现代〕
胡续冬〔现代〕
崔义君的小诊所隐秘地夹在服装街
和饮食街的结合部,象腋臭一样
散发着从温饱到小康的小跑运动分泌出的
难言的气息。
污渍斑斑的塑料门帘
掩不住小城市的苍蝇爱看热闹
的劣根性,它们交头接耳,在弃物桶上
议论着重庆发廊妹的白带之谜,并把起因
推溯到扎在黄陂老板身上的那针“淋必治”
是否过期。
我未来的姐夫崔义君
发家致富的香烟薰细了曾在医学院里
终日昏睡的双眼,疏松的笑脸象是
过早烤熟的面包,从中可以闻到
美味的而立之年应有的配方:
只需把
大厨福柯的知识加权力改换为本地出产的
学历和人际关系。
“而这十平米的中西医结合
曾为我市的繁荣挽救过多少积劳成疾
的小业主,多少晚节难保的老干部。
”
今年夏天,久咳不止的我也曾一度来此
接受崔义君鸡同鸭讲的诊治。
透过
输液瓶里夏瑜那液态的人血馒头,
我看见门口“华佗再世”的招牌附近
愤世嫉俗的肉铺掌柜正在等待编织匠和卖枣人
的到来,而下岗的弗拉基米尔和前劳改犯
爱斯特拉岗,又已在电线杆下枯坐了一天。
98.9
 食指〔现代〕
食指〔现代〕
 赵熙〔现代〕
赵熙〔现代〕